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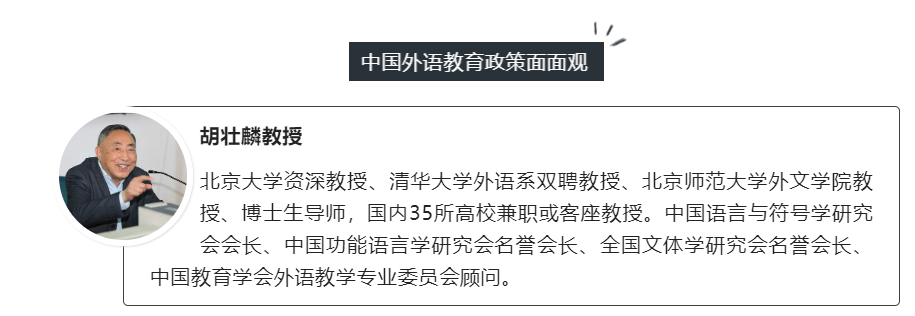

国家政策的全面规划和指导作用 2020年末,我受邀参加了青岛大学召开的外语教育改革线上会议。我发言的第一点不是讨论外语教育改革的具体问题,而是要求主办方首先肯定国家有权了解和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指导我国中小学和高校的外语教育(胡壮麟,2021)。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我曾接触到一些外语教师,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当走西方教育的道路,独立自主,政府无权干预。这个片面认识不解决,我们在会上发表任何观点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事实上,早在解放前,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便规定上海的各个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便在全国准备教育改革。1952年在全国实行高校院系调整。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改成工科大学,于是清华“外文系”下属的俄语组、英语组和法语组,分别合并到新北大的“俄语系”和“西语系”。这样,我原为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的学生,那时又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这完全是国家政策起到决策和引领作用。 再进一步看,人们过去熟悉的“外文系”改成“外语系”,这是因为解放前强调“文学”教学,改革后的“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强调“语言”教学,因而“语言”放在“文学”之前。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自1987年起的改革开放,教育部当时并没有放弃“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这个概念。 在此我要强调一下,不仅是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资本主义的西方大国政府也有自己的教育战略和政策。就美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而言,笔者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过“美国的语言问题和语言政策”(1993)和“美国的双语教育”(1994)二文。2018年,又写过“美国新世纪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一文。在该文中我曾提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美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共和党在国会中多次提出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以英语为美国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如“英语赋权法”“英语统一法”,只是这些提案均未获通过。为了提高仅具备有限英语口语能力学生的英语水平,美国国会和政府先后将“双语教育法”改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每个学生都成功法”,美国教育部则推出“英语习得、英语提高和学术成就法”。据报道,奉行这些政策后,美国学生英语水平确实有所提高。美国宪法也容许各州政府拥有自己的语言政策和官方语言,自1990年以来新增15个州和地区把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连前共计29个州和地区。 美国的汉语教育情况主要由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掌握。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2017年7月1日的调查报告,汉语作为外语日益受到重视。汉语在中小学的语言教学中已是第四大外语,使用人数还在继续增加。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则报道,美国有4000所中小学开设不同类型的中文课,如选修课、高级预备课程、小学中的双语教学等,由各学校自行决定,主要教授简体汉字和标准普通话。此外,全国有500所民办中文学校,学生20000多名。规模最大的是1995年开设的华夏中文学校。至2016年底,美国已有110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位居第一。 02 专业方向1:文学、语言、翻译 应该承认,我国解放前高校的外语院系以开设各种文学课程为主。即使学生没有从事文学教学、研究或翻译的意愿,也得通过学习文学课程来提高外语水平,即通过“走文学道路”学习外语。我本人中学时的志愿是长大后成为像肖乾那样的著名记者,但我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后,一位邻居建议我先学好英语,才能成为奔跑国内外的名记者,于是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学英语。 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学外语小说不是学习外语的唯一道路。解放前我所念的上海市私立圣方济中学是所天主教学校,所采用的英语教材不是英美小说,而是美国记者Washinton Irving所编辑整理的散文集The Sketch Book(《见闻札记》)。甚至1953年毛主席提出“三好”后,为了实现“学习好”,我首先想到的是复习中学时期那本教材The Sketch Book。两年前,我为黄必康教授《英语散文史略》积极作序,表达了我对他从事散文研究的赞许(黄必康,2020)。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首次提出“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这个完整概念,虽然保留“文学”二字,从排位上“语言”放在“文学”之前。其次,作为教学单位“外语语言文学系”简称“外语系”,不再是“外文系”。不难看出,国家对外语教学的目标,更为重视“语言”。 1953年末,我有机会了解到北大有些文学教师向教育部提过意见,如何发挥北大的“文学”优势。教育部研究后同意1954年进校的新生有一部分可以“文学”作为重点培养。我认为,这是外语专业学生分为“文学”和“语言”两个方向培养的最早起因。改革开放继承了这个传统。 在本节标题中,我提到“翻译”,因为“翻译”二字很早便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我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中。早在1950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英文组后,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向我们新生谈话时,明确告知我们,由于国家对外语,特别是“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我们这批新生是按“翻译”方向培养的,因此清华外文系将不给我们开设过多的文学课程。事实的确如此。1952年秋,我作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本科生便被借调至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代表人数达60多人的印度代表团翻译。毕业后,我先后在总参二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过“翻译”的职务。当时有一点我不太理解,不论是1952年院系调整,还是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教育部都只提“外语语言文学专业”,不提“翻译”。后来从非正规渠道获悉,我国外语界的一些资深教授认为“翻译”只是实践,没有理论,不能成为专业方向(胡壮麟,2020)。 退休后,我在本世纪初了解到教育部已确认“翻译”的专业地位。我注意到,许多高校不仅设置了“翻译专业”,还成立了“翻译学院”。我也注意到,翻译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理论性。许多期刊均设有翻译研究专栏;专门的翻译研究期刊有“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翻译季刊”“编译论丛”“上海翻译”“语言与翻译”“东方翻译”“翻译界”“外语与翻译”“译苑新谭”等。这说明翻译不仅是一门外语专业的教学课程,而且有值得重视的“翻译学”。这完全得益于教育部的英明之举。 我们国家最近制定了若干涉及“翻译”的新政策,如科学研究中强调“本土化和国际化”,既要将引进的国外先进成果能适合中国本土情况发挥作用,也要将中国本土的先进成果向国外报道,获得国际上的公认。不难看出,“国际化”离不开不同语言的交流和相应的“翻译”。就我熟悉的语言学理论而言,我们熟悉国外学者的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本土化”,但国外很少谈到中国语言学家的成果。不久前,我写过论文谈及我的导师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有不少源自中国语言学家王力、罗常培、高名凯等的观点(胡壮麟,2018)。有的学者不表赞同,其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将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发表,因此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学者的成果。其次,有些问题要深入分析。韩礼德在论文中为什么不引用中国学者的成果?他有他的苦楚,一是他要多引用他的英国导师Firth的论著,二是50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仇视和歧视。我很高兴,为了支持“国际化”的政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这几年启动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杨敏教授翻译我《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一书已经立项。 我的再一个看法是,有必要分清外语教育和母语教育的区别。上述问题之所以难以统一认识,在于有的外语教师过分强调走英美大学的道路,要求把中国大学的英语系按英美国家大学的英文系的课程设置处理。事实上,国外许多外语教师的认识比我们清楚。我曾经与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讨论。他认为美国大学一般设立“英文系”,因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但汉语是外语,因此成立“汉语中心”。他们开设汉语课程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政治、文化、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懂汉语的人才。可见我们国家的“英语系”既不能办成与国外一样的“英文系”,因为英语在我们国家是“外语”,也不能办成和我们国家一样的“中文系”,因为英语不是我们国家的“母语”。 03 专业方向2:文化和国别研究 1993年初,教育部外语处处长来北大,召集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和英语系的系主任座谈,介绍“文化”的概念和作用比“文学”更为广泛深入,因而动员我们将传统的“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改为“外语语言文化专业”,管理单位由“外语语言文学系”改为“外语语言文化系”。遗憾的是,我们当时的认识远远跟不上教育部的领导,因而讨论的结果是,西语系和俄语系不表同意;我作为英语系主任,害怕引起英语系的文学教师的不满,说了一句态度极不明朗的话:“最好不要更改系名,但我们会服从教育部的最后决定。”令人钦佩的是东语系主任叶易良在会上明确赞同教育部的倡议,并在会议后与季羡林、陈嘉厚等进一步商量,最后把“东方语言文学系”改名为“东方语言文化系”。若干年后,听说又改成“东方学系”。 教育部处长来北大后没有多久,听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虽然没有更改校名,但学校的英文名称分别改为“Foreign Studies”和“International Studies”。“北京语言大学”则一度改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这些都说明我国的高校积极支持教育部的重大决策,也说明国家在制定全国政策时没有要求各校强制执行,让各校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改革。这体现了“教育自主”的精神。 至于国别研究,我感受最深的是1996年我退休后,在北大外事处工作的领导郝平同志曾先后让英语系金衡山、刘树森、张华、马乃强、刘红中等成立“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组织英语教师从事澳大利亚研究。尽管我已退休,仍动员我老有所为,挂名为中心主任,并为今后召开的一些研究会提供论文。应该说,学校和英语系领导的考虑和决定是正确的,找对了人,因为我在清华本科生期间便参加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具体负责接待印度代表团的工作;在总参二部整理提交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氢弹试验的活动报告,也在《解放军报》发表过美苏军事力量对比研究的文章,后由《光明日报》转载(胡壮麟,1958);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工作期间,正值国内粮食减产的困难时期,我对美国和印度等国的粮食生产情况和经验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亲自去中联部做了汇报。很高兴,我没有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能积极完成下交的各项任务,如1998年10月23—2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第六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我一人递交了两篇论文,“The west review: From the discussion paper to the final paper”和“East Asia crisis and Australia”,并在会后主编了《中澳合作的广阔前景》论文集(2000)。多年后,澳研中心负责人刘树森和刘红中又帮我出版了在各个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共15篇,书名《跨越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2016)。 我还要汇报一下,单北大外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有不少从事与“国别研究”有关的工作,并做出成绩,如1971级的田小刚曾派驻英国任公使衔教育参赞,1975级的刘振民曾任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83级的本科生于红先后任驻尼泊尔大使和文莱大使。这些都说明外语专业培养的学生能从事多种跨学科跨专业的工作。 04 外语院系的设置和语种 我国高校外语院系如何设置?应该讲授何种外语?多少种外语?这决定于政治、科技、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最了解情况,且最有决定权的显然是政府部门和学校领导。 1950年清华外文系录取的新生,俄语组28人,英语组11人,法语组不到10人。这归因于解放后的中苏关系,俄语受到年轻人的重视。学生的政治背景也大为不同,俄语组有一名预备党员和多个青年团员。在此背景下,班会和团支部都由俄语组同学担任,学英语和法语的都是群众。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是教育部领导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外文系都合并到新北京大学的3个外语系。我发现,俄语学生数量最多,独立成“俄语系”;英语、德语、法语合成“西语系”下的3个专业;另有一个系就是原北京大学的“东语系”。可见,俄语之所以独立成系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学生数决定的。 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政府的外语政策有所调整,但没有公开,如北京外国语学院让部分俄语专业学生改学英语。 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高校恢复高考,之后开始招收英语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从当时的一些措施看,英语已替代俄语成为第一外语。教育部制订“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首先在英语专业推行,一方面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谈妥,由英方派遣专家,如Geoffrey Leech教授和Nuttal女士来华,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四地举办讲习班,培训中青年英语教师;另一方面,教育部通过全国统考,派遣中青年英语教师去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进修。中美复交后,美国成为接受进修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政策的开放,有的教师自己与国外高校联系进修,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通过托福考试后出国学习。所有这些,再次促成英语替代俄语,成为我国第一外语。我国中小学也相应地以英语教学为主。 不过,国家政策随着时代和情况的变化,特别是自从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后,我们不仅要与西方大国保持联系,也要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英语以外的外语,传统上称作“小语种”,开始受到重视。教育部提出的“新文科,大外语”最能体现国家外语政策的调整。 以北京大学外语院系的建设和发展为例。1999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外国语学院”,下设“英语语言文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俄语语言文学系”和“东方学系”。随着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新世纪又作了多次调整。到目前为止,除“英语语言文学系”和“俄语语言文学系”保持不变外,“西方语言文学系”已分成“法语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语言文学系”;原来的“东方学系”已分成“阿拉伯语言文化系”“日本语言文化系”“南亚学系”“东南亚语言文化系”“西亚语言文化系”“朝鲜(韩国)语言文化系”“亚非语言文化系”。可以肯定,这些变化或发展是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改革调整的背景下出现的。但我们也可看到,北大成立不同系和对各系的命名是相当“自主”的。 在本节中,我最后就课程设置中的“第二外语”发表一些看法。我国高校要求外语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第二外语,这无可厚非。但我注意到,英语专业学生掌握第二外语的水平,一般没有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学得好,因为后者的第二外语就是英语。他们往往在日后的工作中有更多机会使用国际通用语——英语,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中小学已经学过十年英语。为此,教育部和院校领导能否考虑给英语专业学生适当增加第二外语的学时。 05 跨专业和跨学科 就“新文科,大外语”而言,上一节的讨论偏向于“大外语”。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新文科”要求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跨学科、跨专业知识和能力,以便毕业后能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这是外语教师较为苦恼的问题。谁都明白,当初年轻人之所以报考外语专业,一是出于对外语的喜好,二是对其他科目或是不感兴趣,或是成绩较差。 从学校层面,情况不一。给外语专业学生开设非外语专业课程,这个安排在综合大学好解决,因为综合大学的文理科的设置比较健全。外国语大学就比较困难了,这类学校缺乏理工科的师资。尽管我们倡导不同学校联合办学,但效果不太理想。据说,北京外国语大学曾和清华大学联合办学,发生了双方对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意见不太统一的情况;南京大学的英语专业曾培养过双学位的学生,不料学生毕业时要求毕业证书上只写英语专业,这便于他们毕业后更容易找工作。 这里,不妨仍采用“教育自主”的原则,即政府可以制订各项政策,最后由各个学校根据各自的条件执行或选用,不必千篇一律。各校主管外语教育的领导可以研究一些知识性的跨学科课程,供学生选学,但在学时上,即对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时要有控制,首先要保证第一外语专业的教学。 其次,外语教师应具有“语言智能”和“多元化智能”的认识,即在掌握学习外语的有关智能的基础上,也关注其他智能的学习和培养(胡壮麟,2007)。这就是说,多元智能不仅有助于外语学习,也有助于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其他专业知识。例如,逻辑智能可以帮助外语专业的学生学好“语法”,也有利于掌握其他专业的知识体系,特别是计算语言学,或与理工科有关的工作;空间智能可以帮助学生在不同语境中应用外语,也可以在进行其他工作时,提高应用能力。 再次,有关学校和院系领导应善于调查情况,总结各方面的正负经验,如北京大学教务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散英语专业的公共英语教研室,把公共英语教师三三两两分配到全校各个院系,让他们编写结合这些专业的英语教材并进行教学。这个设想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对不懂这些专业的英语教师难度很大。1983年英语系从西语系下独立成系时,这些公共英语教师又被全部撤回新成立的英语系,其原因不详。前几年,清华大学也让公共英语教师脱离外文系,成为独立单位。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向北京大学了解情况,交流经验。 有关单位的领导也可以主动向有关专家请教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学经验。据我所知,国内外著名计算语言学家冯志伟先生在北大原来是学汉语的,现在成了编制计算机翻译程序的专家。他的成长过程值得我们学习。 06 国际化汉语 尽管本文讨论的是国家外语政策,“国际化汉语”或“对外汉语”也应受到我们关注。一方面我国高校已陆续招收国外留学生,首先要解决汉语教学的问题,对这些外国学生来说,汉语成了外语。另一方面,我们与许多国家合作建立“孔子学院”,虽然主旨是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实际工作中离不开我国高校外语工作者的参与。 我在“改革永远没有句号”一文中,曾就教学方法发表过意见。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强调“背诵”,即“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为了更好地培养国外学生,也应学习和掌握一些国外的教学方法,如交际教学法、功能教学法、认知教学法、语篇教学法等。其次,在介绍或教授中华文化时,应实事求是,不要给人以夸大宣传之感,同时也应熟悉尊重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外人士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不久前,联合国下文推荐汉语为全球通用语之一,这一重大决策更应引起我们重视。 结合“国际化汉语”,顺便谈谈社会上不时提出的保持汉语“纯洁”的争论。这牵涉到汉字准备走多远的战略思想,具体说,如何实现“汉语国际化”。我们知道世界上三大语言为汉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英语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人口总数没有超过中国讲汉语的14亿人口和分布在世界各国6000万讲汉语的人口。由于许多国家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懂英语人口总数又超过了讲汉语人口总数,因此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international language)或“全球通用语”(global language)是最佳选择。有专家研究,英语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它不强调“纯洁”,能从其他国家的语言吸收词汇(Dorren, 2014)。限于篇幅,我只举以下例子: 源语 → 英语 德语 noodle(面条)、seminar(研讨会)、blitz(闪电战)、quartz(石英)、queer(奇怪的)等 法语 air(空气)、place(地方)、hostel(招待所)、very(非常)、castle(城堡)、author(授权)、glamour(魅力)等 意大利语 spaghetti(意大利面)、libretto(剧本)、portico(柱廊)、bank(银行)、manage(管理)等 “汉语纯洁论”者未注意到,汉语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过程。秦始皇统一汉字的功绩应该肯定,但统一后的汉语在和不同民族语言和方言接触中,还是有变化的。根据刘正埮等(2015)编辑的《汉语外来语词典》,现代汉语中的“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权、哲学、金库、美学、背景、环境、医学、艺术、入场券、下水道”等均从日语引进,达1000多词。其实,满清后期中国也派遣不少人士出国,但他们在引入西方词语时的翻译理念强调“译音”,如“沙发、德律风、巧克力”等,而日本强调“译意”,他们发现选用日语中的“汉字”更能达到这个目的。 07 结束语 我在本文中讨论国家外语教育政策,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学校、不同时期、不同视角。总的来说,表达了如下观点:首先,我国的外语教育需要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因很简单,政府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能及时组织人员总结经验、采取措施。其次,各个省市、各个高校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教育自主”应该肯定,这决定于教学的不同背景和条件。这要求上下互相沟通、互相支持。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我们的外语教育政策应当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外语教育政策和经验,应当虚心学习。任何完美的战略和政策毕竟是在充分思考和讨论,并在实践检验中获得成功的;第三,贯彻政府政策并非全盘否定“教育自主”,政府部门需要更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从基层单位和外语教师来说,应主动向领导反映实际情况,协商解决问题。最后,需要分清党和政府的政策与个别领导言行的关系。在出现矛盾时,应以正式文本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