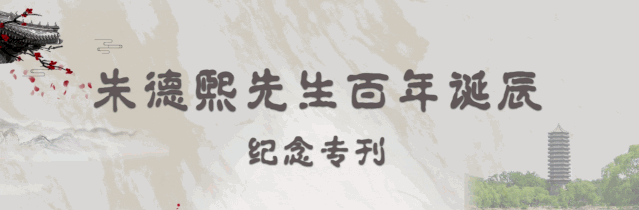

编者按
为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本栏目将梳理跟朱先生相关的回忆文章,以成长、求学、治学、德行、授业、访学、爱情、家庭、交友等主题讲述朱先生的动人故事,展现朱德熙先生的精彩人生。本期刊发陆俭明先生的回忆文章《不忘朱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原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作为“授业”主题的特别篇目。陆俭明先生在文中回忆了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研究、论文写作、课堂教学等方面对自己的指导,具体提到了朱先生的四条教诲:“写文章要重点突出、文字简练”“想问题不要就事论事,要跳出框框,到更大的范围里去考察分析”“形式和意义必须互相验证”“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考虑安排讲授内容,设计课堂教学”。以上四点,不仅是朱陆师徒的学术传承,也是朱先生留给整个汉语学界的财富,至今仍值得青年学人学习和借鉴。

朱德熙先生(中)、陆俭明先生(右)1987年在广州中国语言学会第4届学术年会上
我经常到朱先生家请教问题,朱先生从不拒绝我的访问,总是热情接待。朱先生很喜欢讨论问题,我们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半天。讨论到精彩的地方,朱先生会失声大笑。每次从朱先生家出来,我都感到有很大的收获。是的,我忘不了朱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我毕业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的”的分合问题及其它》(《语言学论丛》第五辑,1963年),这篇文章就是在朱先生指导下写出来的。1961年朱先生发表了《说“的”》一文,文章对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的”作了新颖而又独特的分析,其分析法和结论跟传统语法大相径庭。因此,文章一发表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围绕《说“的”》开展了一场讨论。当时多数人站在传统的立场对朱先生的分析和结论持否定态度。我完全赞同朱先生的意见,对当时别人发表的文章我作了一万多字的笔记,对种种不同意见进行评论。我把这一万多字的笔记给朱先生看了,请他提意见。朱先生看得很快,一个星期后就把笔记还给我了。他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说“你也可以写文章参加讨论嘛”。我说:“行吗?”朱先生说:“怎么不行?你写,写了我给你看。”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写了一篇一万二千字的文章,题目是《也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朱先生仔细地审阅了我的文章,批改得很细。他对我说:“你写得很认真,也还比较清楚,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二是说话啰嗦,不简洁。另外,题目不好,不要用这样的大题目。”朱先生严肃地说:“写文章一定要重点突出,一篇文章要有个中心,集中谈一两个问题,谈深谈透,不要面面俱到。”朱先生帮我分析了当时的讨论,说:“讨论的中心有两方面,一是‘的’的分合问题,一是语法单位同一性问题。我建议你就集中谈这两个问题。”朱先生还帮我定了题目,叫我重写。我按朱先生的意见重写以后,朱先生又帮我修改了一遍。朱先生改得很细,从内容到文字,到标点符号。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我得益匪浅,主要有两点,一是文章内容一定要重点突出,二是文字一定要简练。这两点对我后来写文章很有影响。
1985年我发表了《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这篇文章也是在朱先生的直接关怀、指导下写成的。1975—1976年我教越南留学生现代汉语语法,有个学生问我,鲁迅的《孔乙己》开头一句中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这个偏正结构该怎么切分?当时我凭直感,告诉他,应分析为“鲁镇的酒店的/格局”。这个偏正结构有些特点:(1)在这个偏正结构中,除了“的”,是三个名词“鲁镇、酒店、格局”;(2)第一个名词“鲁镇”与第二个名词“酒店”之间是领属关系,第二个名词“酒店”和第三个名词“格局”之间也是领属关系。由这个偏正结构,我得出了一个想法:包含三个名词的偏正结构中,如果名词之间依次有领属关系,那么在层次构造上一定是左向切分的。1981年在成都举行中国语言学会第一届年会,有一天晚上我到朱先生房间聊天,说着说着又谈到语法问题上去了,我就把对“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的分析以及我的想法说了,问朱先生这样考虑对不对。朱先生说“有道理”,可是与朱先生同屋的李荣先生立即提出异议,他说:“那不见得,譬如说‘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你说一定切分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那不一定,我们也可以切分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因为‘父亲的父亲’就是祖父,按你的切分是‘祖父的父亲’,按后一种切分是‘父亲的祖父’,而‘祖父的父亲’和‘父亲的祖父’等值,都指曾祖父,可见这两种切分都是可以的。”李荣先生的一席话把我说得楞住了。从成都回到北京后,我老考虑着这个问题,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合乎事实的,但李荣先生的例子怎么解释,又想不清楚。我又去找朱先生讨论,朱先生说我也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李荣先生的例子也确实是个问题,我看你去研究研究。”接着他又说:“你一定不要就李荣先生的例子就事论事,一定要跳出框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考察分析。”朱先生这个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想,“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这个偏正结构里的名词都是指人的名词,我应该按朱先生的话去考察由指人的名词组成的偏正结构。我把这个想法又跟朱先生谈了。朱先生肯定了我的想法,并进一步指导我,要我先从包含两个指人的名词的偏正结构考察起,然后扩展到包含三个、四个、五个或更多的指人的名词的偏正结构。我就按朱先生所指的研究路子一步一步研究,结果不但发现指人的名词可分四类六组,而且发现了这四类六组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成偏正结构的六条规则,根据这六条规则证实了我原先的想法,即使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也还是应该切分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这样的切分是错误的。我把文章初稿写出来后,送朱先生审阅。朱先生比较满意,但指出,你不能光说分析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错的,还应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错的,这样就比较完美了。我根据朱先生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又请朱先生看,直到朱先生点头为止。不难看出,我这篇文章也是在朱先生指导下一步一步写成的,而朱先生关于不要就事论事,要跳出框框,到更大的范围里去考察分析的思想也一直指导着我后来的研究。
1983年,以朱先生为首成立了一个沙龙,讨论语法问题。开始参加的人就朱先生、叶蜚声、马希文和我四个人,后来郭锐和马希文的研究生也参加,有一次孟琮、史有为也来参加讨论。我们差不多一星期讨论一次,一般都在晚上,每次都讨论到12点多。有一次讨论到深夜一点半,直到朱师母出来提醒我们才散会。在有一次会上,谈到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时,朱先生认真而又诙谐地说:“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义,那只能是废话;如果光注意意义而不注意形式,那只能是胡扯。”稍停了一下,朱先生接着说:“形式和意义必须互相验证。”那时我正在研究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语法学界一共提到以下四个:啊、吧、呢、吗。但大家看法并不一致。大家对“吗”没有分歧意见,都认为是疑问语气词;对“啊、吧、呢”就有不同看法了。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持哪种意见的,都没有正面说明理由,给人的印象是,只要能在疑问句末尾出现就是疑问语气词。现代汉语中到底有哪几个疑问语气词?说“吗”是疑问语气词,根据是什么?“啊、吧、呢”到底是不是疑问语气词?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朱先生上面一席话给我研究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提供了理论指导。后来我在研究中就一直注意遵循着朱先生关于“形式和意义必须互相验证”的原则,具体说,我在判断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不是疑问语气词时,不根据语感,而看它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这一点又力求在形式上得到验证,验证的办法是比较,那就是从疑问句和非疑问句,从这种疑问句和那种疑问句之间的最小对比中,来确定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否负载疑问信息。我运用上述分析原则,逐个讨论了各家提到的那四个语气词,最后写成《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一文(《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有两个半:“吗”“呢”和半个“吧”;“吧”介乎疑问语气词和非疑问语气词之间,是一个表示“疑信之间”的语气词。这篇文章写出来后,得到了朱先生的肯定,他说,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走这样的路子。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在以后所写的文章中,我都比较注意贯彻朱先生所提倡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
在教学上,朱先生也给了我很深的影响。1961—1962年第二学期,我接受了教汉语专业学生现代汉语语法的任务。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给本专业学生上语法课。在寒假里,我去朱先生家请教问题,谈论中间我问朱先生:“大家都说你的课上得好,把语法讲活了,学生都爱听你的课,这有什么诀窍没有?”朱先生谦虚地说:“哪里,哪有什么诀窍。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那就是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考虑安排讲授内容,设计课堂教学。”从这短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朱先生对教学的高度的责任感。朱先生在授课前对讲授内容、课堂教学都是精心作了安排和设计的,而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为了让学生便于接受,更好地掌握。朱先生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在我后来的教学中,除了注意学习朱先生的课堂艺术外,就一直把朱先生说的“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考虑安排讲授内容,设计课堂教学”的话作为自己教学上的座右铭。
要说我在教学、研究上有些什么成绩,都跟朱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朱先生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导师。我一定不忘朱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更大的成绩,以告慰朱先生在天之灵。

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79级毕业合影(二排左四为朱德熙先生,三排右四为陆俭明先生)
